《大师》剧情介绍
大师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1949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结束,备受军中无聊生活困扰的弗雷迪·杰奎(华金·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 饰)终于返回美国,然而返家前的精神治疗没有给他实际的帮助,弗雷迪陷入了一种恍惚乏味的人生体验无法自拔。次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工作失败后,弗雷迪在醉后登上的客 船上结识了经历复杂的“大师”卡斯特(菲利普·塞默·霍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 饰)。卡斯特建立在时间理论之上的精神治疗法引起了弗雷迪的兴趣,在卡斯特的“引诱”下,弗雷迪尝试敞开心扉,寻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并越来越亲近卡斯特松散的“缘教”组织,为其摇旗呐喊、打击异议者。在“治疗”过程中,弗雷迪与卡斯特的关系分分合合,愈发复杂……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让学生人生重生的学校边缘状态果阿猎人白河警事纠缠太阳不西沉哈林四女子第一季浪漫鼠德佩罗儿女传奇之选美请融化我搭车遇狼惊魂记等候董建华发落边山北地猎人周末不上班互怼特工华沙间谍生命的力量旮旯山军犬麦克斯2:白宫英雄优雅的家长空铸剑杰姆·耶尔马兹:招牌笑料2024雷霆沙赞!众神之怒拉斯维加斯往事战斗传教士断线之后铁男3:子弹人电台之星嘿!你大事很妙
1949年,太平洋战争已经结束,备受军中无聊生活困扰的弗雷迪·杰奎(华金·菲尼克斯 Joaquin Phoenix 饰)终于返回美国,然而返家前的精神治疗没有给他实际的帮助,弗雷迪陷入了一种恍惚乏味的人生体验无法自拔。次年,在经历了一系列工作失败后,弗雷迪在醉后登上的客 船上结识了经历复杂的“大师”卡斯特(菲利普·塞默·霍夫曼 Philip Seymour Hoffman 饰)。卡斯特建立在时间理论之上的精神治疗法引起了弗雷迪的兴趣,在卡斯特的“引诱”下,弗雷迪尝试敞开心扉,寻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并越来越亲近卡斯特松散的“缘教”组织,为其摇旗呐喊、打击异议者。在“治疗”过程中,弗雷迪与卡斯特的关系分分合合,愈发复杂……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让学生人生重生的学校边缘状态果阿猎人白河警事纠缠太阳不西沉哈林四女子第一季浪漫鼠德佩罗儿女传奇之选美请融化我搭车遇狼惊魂记等候董建华发落边山北地猎人周末不上班互怼特工华沙间谍生命的力量旮旯山军犬麦克斯2:白宫英雄优雅的家长空铸剑杰姆·耶尔马兹:招牌笑料2024雷霆沙赞!众神之怒拉斯维加斯往事战斗传教士断线之后铁男3:子弹人电台之星嘿!你大事很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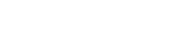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看的过程一直在走神。这片儿显露出巨大的野心,巨大到盖过了其他一切——也许除了Hoffman的表演。摄影剧本剪接主题都是“优等生”,但在表情达意恰恰是我本人最讨厌的那个路数——过于卖弄机巧企图俯视而失了诚恳,拒绝跟观众交流。PS:Amy和凤凰凑一起互相影响都演得好紧,看得我好难受!
前半段是“我没有信仰,我好痛苦”,后半段是“信仰让我好痛苦”,最后恍然大悟,痛苦不过是有人治疗我的时候我放弃了爱情,我挽回爱情的时候放弃了治疗。爱情和信仰都抛弃了他,但这之前,他先抛弃了情人和大师。
其一是因为不喜欢这个霍夫曼,不管角色是什么样子的人,每次看他演男配都能演出同一个调调。没气场的他根本就没法驾驭Master,不知是不是导演选角的有意而为之。其二,如果科学教真是如此,那真是逊爆了。其三,我根本不明白电影想说什么。
老实说没看懂,幸好当初没为了cineplex的3倍积分而买票进电影院看
对这部真是极度无感。
大师,你又在故弄玄虚了,大师。
先不吐槽PTA还是有些刻意还有想当然的手法... 主要是为毛我在一个胖子的演技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叫做"统治力"的东西,然后这让凤凰哥在胖子面前表现出的不像是癫狂也不像是歇斯底里而更像是无头苍蝇似的演技。
大约探讨了人的精神困境(失控与失调)以及宗教(在这里多少披着精神分析的现代外衣)的形成过程与社会功能。1,宗教不是科学,将宗教说成科学的与用科学论证宗教一样是没有意义的。2,教主与信众是相互成全的,他们相互需要。3,绝大多数情况下,人需要权威,需要归属,需要精神的家园。4,信则灵,不代表信仰就是假的,你不相信,不代表别人相信就是错的。只有信与不信之分,而无真假对错之别。影评里提到“imagine”代替“recall”,的确也有意味。
这当然是部好电影!
我就是觉得很难看,还有很讨厌他的摄影手法。
200+的厅基本满座 5人左右离场
没懂。。。
最後 , 變了的原來是自己~!!!
不要看。强烈不推荐。整部片子里充斥着无缘无故的暴力和愤怒和奇怪的色情场景。难以置信居然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了那么多奖。
出神入化的表演,尤其是杰昆。镜头很美,只是故事有点欣赏不能。
没看明白主题是啥
没看懂。虽说演员都是喜欢的。
Hoffman的表演大好 凤凰与之相比有些用力过猛鸟!
有点深奥啊。。。
有点冗长,当邪教头目真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