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剧情介绍
杀戮演绎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1965年,印尼政府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都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并遭遇了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共产党人”丧命,其中就包括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的元老人物。Anwar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Anwar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就包含着他年轻时候对美国黑帮电影的喜爱,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第二次人生第二个问题:你是谁?BuddyComplex靠近我一点无尽的月兵变1929戏里戏外第一季兔侠传奇听见你的声音两代在她们眼中天渠重庆谍战天王助理我将消失在黑暗中偷狗的完美方法凯利党杀人合约中华兵王之警戒时刻大错特错地下室惊魂良药苦口东北告别天团不可思议的夏天保罗石墙小鬼上路半径5米我们都不完美末基劳:英雄崛起
1965年,印尼政府被军政府推翻,那些反对军事独裁的人都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并遭遇了血腥屠杀,一年之内,就有超过100万“共产党人”丧命,其中就包括农民还有一些当地的华人。本片的主角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就参与了当年的屠杀活动,他如今是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的元老人物。Anwar和他的朋友接受导演的邀请,在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他们是如何处死那些“共产党人”的,他们通过拍摄电影的方式,重现了当年的场景,再次拿起了那些沾满鲜血的用来勒死人的铁丝。Anwar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就包含着他年轻时候对美国黑帮电影的喜爱,而他所属的准军事组织Pemuda Pancasila虽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力量,恰恰也被人视为印尼最大的黑帮......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第二次人生第二个问题:你是谁?BuddyComplex靠近我一点无尽的月兵变1929戏里戏外第一季兔侠传奇听见你的声音两代在她们眼中天渠重庆谍战天王助理我将消失在黑暗中偷狗的完美方法凯利党杀人合约中华兵王之警戒时刻大错特错地下室惊魂良药苦口东北告别天团不可思议的夏天保罗石墙小鬼上路半径5米我们都不完美末基劳:英雄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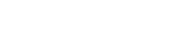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华人应该记住.
可怕
选题不错,原以为会是个有难度的片子,实则不然,印尼佬不以为耻,就算Congo再卖力干呕(做作恶心),换哪个欧洲面孔去拍,他们还是反以为荣的,所以拍摄能力上无法体现水准。看的是导演剪辑版,可看性极低,啰嗦而杂乱的流水账,想要揭示的问题也仍然浮于表面,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Ugly both in skin and in soul, they'll be down to shrimp, and ate by the weakest creature, just as the opening scene.
三观扭曲。杀人者以重演杀戮的方式获得乐趣这些人生活得这么安稳对这个世界来说都是讽刺
搞不懂,为什么要拍一群杀戮成性的人的内心救赎,哭了就真正感受到别人的痛苦啦?记录片拍的表演成分真的太强了,穿插着一种超现实的人物演绎色彩。现实生活里地方政府控制一切不畏舆论,民众一群草包。
垃圾
《杀戮演绎》——荒诞和喜感的背后是一场屠杀,刽子手至今言称并无愧疚,但从他们的眼神就举止中你会发现忧虑和恍惚,本片没有夹带任何拷问,一切由当事者呈现,他们享受表演的乐趣,冷静和戏谑中让人不寒而栗。
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
好造作!简直不敢相信是纪录片!
杀戮即罪恶,权力即道德,忏悔必得换位而心有畏惧。真相并非都是正确,判定的宏观与微观又如何跨越。表演为虚构,但演出者和事件为真实,act结束后的欢庆在虚实交错间人性一览无余。纪录片总让观者愤怒与反思却无能为力,当事人依旧在自己的运作轨道里延续。人种和文明确有优劣之分。
mind-blowing masterpiece. hilarious and blood-chilling. images of violence in film, image making in politics, images as a way to reassure and deal with guilt
无语,愤怒,震撼!离文明那么近,又离文明那么远
知道它是很沉重的题材,没想到过程这么讽刺就是了,整个一个cult片聚会啊,吃惊。片中各个人物都令人印象深刻。EP是Errol Morris和赫尔佐格
电影是人的情绪,电影史是人的情商演化史。所以该片是大烂片
莫名想到电影斗士中,电视台告诉男主要拍他的职拳传记片,结果最后剪成了戒毒宣传片。
拍摄电影即作为记录的由头,又协助当事人回忆,形式上呈现主观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行为介入法对当事人的反作用力,赫尔佐格当然喜欢面对疯子时这些略带疯狂的尝试,只是因此片子最后的反省情节是可疑的。
。。。看了开头骂赤色份子那,我就不敢看了,怕查水表
最痛苦的感受是满腔的怒火居然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变成了无奈和麻木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