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花之雨》剧情介绍
腐花之雨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影片改编自松浦寿辉获得芥川奖的同名小说,由荒井晴彦执导,讲述奋斗在逐渐衰落的桃色电影界的导演栩谷(绫野刚 饰)和立志成为编剧的男人伊关(柄本佑 饰),以及两人所爱的女演员祥子(佐藤穗奈美 饰)之间悲伤而纯粹的恋爱故事。三人所怀抱的对电影的梦想逐渐崩溃,他们各自的人生也开始相互交错。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戏杀芊叶长笙伏魔篇选票风波假面骑士帝骑#家族募集茶缘叫作你的秘密美丽的他第二季天啦妈妈的使命点穴侠远亲八分钟的温暖金钱豹子汤隆叶问前传芥子时光我的男友是雕像夜半凶宅里长与郡守希望的诞生皮囊第一季危险因素大师尊严:真枪实弹蓬莱间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游戏规则牙狼:钢之继承者发现大丝路乱世护宝
影片改编自松浦寿辉获得芥川奖的同名小说,由荒井晴彦执导,讲述奋斗在逐渐衰落的桃色电影界的导演栩谷(绫野刚 饰)和立志成为编剧的男人伊关(柄本佑 饰),以及两人所爱的女演员祥子(佐藤穗奈美 饰)之间悲伤而纯粹的恋爱故事。三人所怀抱的对电影的梦想逐渐崩溃,他们各自的人生也开始相互交错。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戏杀芊叶长笙伏魔篇选票风波假面骑士帝骑#家族募集茶缘叫作你的秘密美丽的他第二季天啦妈妈的使命点穴侠远亲八分钟的温暖金钱豹子汤隆叶问前传芥子时光我的男友是雕像夜半凶宅里长与郡守希望的诞生皮囊第一季危险因素大师尊严:真枪实弹蓬莱间完美先生和差不多小姐游戏规则牙狼:钢之继承者发现大丝路乱世护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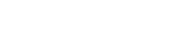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为瑞秋·布罗斯纳安而来 !她在《了不起的麦瑟尔女士》里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