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词》剧情介绍
同义词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约亚夫(汤姆·梅西尔 Tom Mercier 饰)是一名以色列退伍军人,他非常向往法国浪漫而又开放的风气,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结果却惨遭打劫,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对艺术家情侣卡洛琳(昆汀·多尔马尔 Quentin Dolmaire 饰)和艾米勒(露易丝·谢维洛特 Louise Chevillotte 饰)向约亚夫伸出了援手,令他免于流落街头的厄运。 经此一劫,约亚夫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拒绝再说母语,通过背同义词的方式学习法语。很快,约亚夫就发现,卡洛琳和艾米勒虽然对自己表面友善,但其实是在利用他。约亚夫在战场上的悲惨经历成为了艾米勒创作的养分,而卡洛琳则试图通过约亚夫强壮的身体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性欲。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斗转乾坤共饮一江水总裁在上3:换子疑云无主之地阿尔泽鬼影敲门越狱特别篇:最后一越编号17保你平安懒女苏珊美洲豹利刃出鞘3校园犬神2内森的王国当男人恋爱时即便明天世界终结推拿狩猎游戏三姐妹少年天子咕噜咕噜小动画剧场恐怖假日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篮球纪之我想打篮球波斯王子:时之刃京城怪物午夜之后老捕快玛格丽塔彩虹时分
约亚夫(汤姆·梅西尔 Tom Mercier 饰)是一名以色列退伍军人,他非常向往法国浪漫而又开放的风气,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了巴黎,结果却惨遭打劫,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对艺术家情侣卡洛琳(昆汀·多尔马尔 Quentin Dolmaire 饰)和艾米勒(露易丝·谢维洛特 Louise Chevillotte 饰)向约亚夫伸出了援手,令他免于流落街头的厄运。 经此一劫,约亚夫决定彻底放弃自己的国籍和身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法国人。他拒绝再说母语,通过背同义词的方式学习法语。很快,约亚夫就发现,卡洛琳和艾米勒虽然对自己表面友善,但其实是在利用他。约亚夫在战场上的悲惨经历成为了艾米勒创作的养分,而卡洛琳则试图通过约亚夫强壮的身体来满足自己无穷无尽的性欲。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斗转乾坤共饮一江水总裁在上3:换子疑云无主之地阿尔泽鬼影敲门越狱特别篇:最后一越编号17保你平安懒女苏珊美洲豹利刃出鞘3校园犬神2内森的王国当男人恋爱时即便明天世界终结推拿狩猎游戏三姐妹少年天子咕噜咕噜小动画剧场恐怖假日爱·回家之开心速递篮球纪之我想打篮球波斯王子:时之刃京城怪物午夜之后老捕快玛格丽塔彩虹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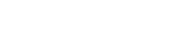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以为是GAY片结果看了2个小时男主都没和男二啪啪,反而把男二女友啪了两次?
男主这屁股 绝了
Nadav上一次是诗,这一次是字典。虽然设计感有些重,但是那些被讲滥的话题(移民问题、身份认知 etc.)和令人不安的真相(PTSD、以黎冲突 etc.)都在调度下有了新的角度和讨论。并且始终跟随Yoav的愤怒、焦虑和离开,投入到故事中去。PS 这个电影拍得忒“gay-baiting”了一点,那些“finger play”那些裸露那些和Emile看得人有些脸红,甚至产生了自己是不是太骚了的疑问。
法语片劝退,真的!别抱幻想
如果有人呐喊,他们就演奏乐曲
看看肉就好,不想动脑思考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离开家乡去寻找白月光,到头来什么都没了。
本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继《系统破坏者》之后另一部主角衣服出彩的影片。个别场景确实很令人回味,但没别的感想了。3.5
在电影院里笑最大声的,正是法国最虚伪最腐朽的所在。
非常喜欢,摸在地毯下的那个钥匙让他丢失了所有,他以为找到了一扇打开的门,到头来那扇门从不会为他而开。
有病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非线性的首尾相接,没有人物情绪的弧光渐变,仅有瞬时的状态粉碎。将人种(身体)、民族(文化)、国籍(语言)这样的二维身份标识进行拼贴,升维成立体的“人”,再以阶级之刃完成降维打击。生产资料多寡的失衡击破分配关系的假象,是利用不是交换,是索取不是共享,历史是厚重却干瘪的,当下是浅薄却致命的。影像和文本一脉相承,诱导性、欺骗性、冲击性和频繁的虚晃一枪,摄影机无处不在,抖动与跳接不是制造幻象,而是掩盖骗局。
美国梦看得多了,法国梦又有不同。主角的造型、语言、能够做的选择和行为途径都同影片叙事一样,被独立且和观众有距离感,与反复敲门的动作形成一致。有趣的是作为导演的半自传,戏中主角作为“说故事的人”的失败与戏外导演作为“说故事的人”的成功(金熊)形成了某种奇特呼应。
很大。然而…啊?
身材不错啊,真好看。文化差异思想观念的差异注定不能融入当地社会,终于要爆发。其实这样的人我也不敢接触,差异就是雷区,不小心就触雷,伤害彼此。俩正装男办公室打斗那段我还以为是拍men at play 呢
用尽全身力气,可始终也撞不开那扇门。
一个以色列军人逃到巴黎,决定背弃自己的国家,再也不说希伯来语。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法语,用远高于日常生活需求的书面、诗意而怪异的法语讲述自己的过往,一串串从字典里习得的同义词仿佛一个个子弹,向着自己的身份历史开枪。叙事极端不可预测,表演极具身体性,不同的摄影风格、多样的取景选择成就了这部导演半自传电影的多义性与复杂性。也就是说,这一定是一部好恶严重分化的电影。在显而易见的政治主题之上,这是一部罕见的、关于词语的电影。反思以色列,也反思法国。
手持晃得我头晕皮囊是好,工具罢了
用力过猛的地方让它开始变得很无趣,实在不够轻盈。和《教师》一样,机位的摆放挺有他自己的风格,但有些分镜做得略潦草或我理解不了。(PS,导演去哪里找到这种宝藏男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