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洛》剧情介绍
塔洛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孤儿塔洛牧羊维生,他是记忆世界的国王,记得所有的事情,但他却是真实生活的边缘人,没人记得他,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只唤他小辫子。直到他遇到理髮馆女孩,第一次被人记得,第一次爱,那就是存在的开始。塔洛开始一场爱情,很多惊奇,大多失望,见天地,望众生,然后回到自己。辫子失去了还会长回来,那关于这个世界呢?总是需要一次离开,然后才知道归来。 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短篇小说,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麽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武士的食谱银湖之底十全大补男大小笑探致命名单细思极恐微光湖脆弱所念皆如愿我们之间的距离诚忠堂九个完美陌生人第二季退货儿童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永远与自动手记人偶宇宙中最明亮的屋顶刑警使命黑暗复仇者狙击手:逆战三国恋夺命护士小财迷蛇头乱反射插翅难逃壮丁也是兵闪点行动第三季卡蜜儿若影若线难道就只有我心动吗第22条婚规
孤儿塔洛牧羊维生,他是记忆世界的国王,记得所有的事情,但他却是真实生活的边缘人,没人记得他,连他的名字都忘记了,只唤他小辫子。直到他遇到理髮馆女孩,第一次被人记得,第一次爱,那就是存在的开始。塔洛开始一场爱情,很多惊奇,大多失望,见天地,望众生,然后回到自己。辫子失去了还会长回来,那关于这个世界呢?总是需要一次离开,然后才知道归来。 改编自导演万玛才旦短篇小说,聚焦藏人生活景况,以黑白影像粗粝质感勾勒出西藏大地的苍凉,更缩影这一代藏族青年的内心迷惘。在心灵的高原上壮游,以为走得那麽远,其实仍踌躇传统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欲离何曾离,云空未必空。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武士的食谱银湖之底十全大补男大小笑探致命名单细思极恐微光湖脆弱所念皆如愿我们之间的距离诚忠堂九个完美陌生人第二季退货儿童紫罗兰永恒花园外传:永远与自动手记人偶宇宙中最明亮的屋顶刑警使命黑暗复仇者狙击手:逆战三国恋夺命护士小财迷蛇头乱反射插翅难逃壮丁也是兵闪点行动第三季卡蜜儿若影若线难道就只有我心动吗第22条婚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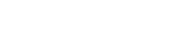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看得我奄奄一息额
压抑又平淡,想打死男主,患了绝症你就天下最大吗?
男友的爱在得病那天就收回了,他谁也不爱,女友独自承受,照料,得绝症的男友到最后一天,那爱成了日常的繁琐直至爱的消逝。面对被一个病痛折磨,身体与精神的亏空的病人,女主是一种无声的孤独,她也想一走了之,但两人的生命力都在消耗,她要亲自画上句号。
很闷。最后看哭了。
奄奄一息
留住有情人
四苦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
本来想看《芳芳》,网站抽风了搜的是芳芳内容是这部。挺喜欢影像风格的就看完了,那种漫长压抑、痛苦和绝望拍得挺好的
勉强看完,演技还可以
Three and a ha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