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偷马》剧情介绍
外出偷马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67岁的老人特罗德痛失所爱,失去了“与人对话的兴趣”,准备退隐山林独居,平静地度过余生。一次与邻人的偶遇,让他又回忆起与父亲在山林中度过的那个夏天,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而他余生的命运也在那个夏天被永远注定。影片由挪威最负盛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佩尔•帕特森代表作改编,影片充分吸收了原著的文学韵律,令观众回味悠长。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罪恶清除工魔导具师妲莉亚不向人低头心跳茂山日记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尔摩斯现在加糖昨日的果实狂野分手团冲向天际勇者恐怖爱情故事之死亡公路你好,我们是欢喜天团狙击之王:暗杀三次元女友第一季不朽的西罗凤凰城等着你第二次初见大路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第四季手册生旦净末丑碰撞搜查线封神战纪神奇动物管理员第三季特种神枪手纯纯的小时光金斯湾我要和你在一起铁血红安司令阿根
67岁的老人特罗德痛失所爱,失去了“与人对话的兴趣”,准备退隐山林独居,平静地度过余生。一次与邻人的偶遇,让他又回忆起与父亲在山林中度过的那个夏天,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父亲,而他余生的命运也在那个夏天被永远注定。影片由挪威最负盛名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佩尔•帕特森代表作改编,影片充分吸收了原著的文学韵律,令观众回味悠长。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罪恶清除工魔导具师妲莉亚不向人低头心跳茂山日记京都寺町三条商店街的福尔摩斯现在加糖昨日的果实狂野分手团冲向天际勇者恐怖爱情故事之死亡公路你好,我们是欢喜天团狙击之王:暗杀三次元女友第一季不朽的西罗凤凰城等着你第二次初见大路联邦调查局:通缉要犯第四季手册生旦净末丑碰撞搜查线封神战纪神奇动物管理员第三季特种神枪手纯纯的小时光金斯湾我要和你在一起铁血红安司令阿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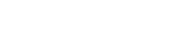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于我而言很是晦涩难懂。
“原来痛不痛,真的可以自己来决定”Trond(主角)和Lars是一组对比。他们同样曾被别人取代,同样经受过意外,区别在于事后是否仍旧被过去所把控着。青年的Trond在最后收住了手,从已然发生的事中挣脱出来,穿上西装,是为成长。导演很爱用前景虚化和背景虚化,以及两者的变化交替。不同叙述线条上的镜头通过色调和季节彼此区分开来。快速的镜头切换加画面的快放加配乐加暴风雨前的自然景象,把情感渲染得很到位。
没看过原著,对居高临下吹毛求疵的原著党鄙视至极。以一个正常观众来看,整部电影完成度很高,是一部难得的文艺佳片。只对个别演员不是很满意,比如那个孩子惨死、妻子出轨的丈夫,太年轻了,完全不胜任角色!
3星半。如河中浮木一样,北欧少年苦楚满怀不断晕菜的夏天。为了暗示自己能够静观不时迸溅如星火的浅表痛楚,我想起自己可是读了三遍安德烈耶夫《七个被绞死的人》的人呐。
北欧国家除去冰岛这实在地太小人太少的 挪威电影的水准最低
【杭州挪威电影展】北欧风景,有时恍如我们的中国山水,在影像中冷峻流逝着,就像这些被伐的木材,随流远漂。旁白把回忆、现实破碎般组建在一起,缓慢的推镜,电影质感竟然十足。跌落马的伤口,哪能比内心的创伤痛苦,鸟蛋的破碎,哪能比生离死别更悲伤,恋母弑父,幸好,那个拳头没有打人,再次落马已不再受伤。痛不痛,可以自己决定!
北欧的电影,一部清冽寒峭的散文诗。节奏缓慢,多层叙事,剪辑跳跃,不容易消化。寡语沧桑的他,性格的根源来自少年时隐秘的记忆。如同伐木拧结在河中,在多年后的冬夜被撕扯开来。那个发生了太多事的夏天,有爱的萌芽,有性的潮湿,有偷的窃喜,有死的殇夭,还有叛逆期里懵懂的俄狄浦斯情结。原来成长就是选择忽视疼痛。
确实偷马了。童年阴影类
不得不承认真的把我看得很困,当然根据诺贝尔文学奖作品改编肯定有它的优异性的,会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旁白也许就是来自小说,但是催眠效果真的太好了。再加上没有看过原著,电影又把时间线剪得特别碎,前后很多剧情在逻辑上的关系也不是很强,一些隐喻看得也比较懵逼,导致整个观影过程真的很疲惫。
回归
秉承了似约阿希姆提尔的自然神秘的北欧风格,多线的穿插闪回增添悬疑也观感疲惫,是男孩的成长也是回忆的伤痕。给每一根原木打上的痕迹,最终都会让你在(人生)长河的尽头找到它。
悬疑片
少年的夏,暮年的冬;暖而不热,冷而不冰。漫漫人生路,最终铭记的季节也好,瞬间也罢,无非逃不开有关成长的一切。步入老年也不是就画上句号了啊。想读原著。
我總是帶著忐忑的心,生怕這在《性上癮》裡晚節不保的老頭最後又幹啥了。
看完跟梵一老师对了一下,发现我们都有几近昏睡过去没看清的情节,没办法这片拍得可真无聊啊。一个大雪山里独居等死的老头,和他青春期与父亲在伐木场的一段回忆。展现了性懵懂、弑父情结、动乱年代背景与世外桃源对比、疏远的亲情关系,但都浮于表面,没作深入挖掘。当然最大问题还是,拍得太催眠了。
男主丧偶,孤身前往深山老林生活,四十多年前,他年少的男主曾在那里度过一个毕生难忘的夏天,他的父亲承包了那个农场,而他爱上了邻居家的女主人。女主人的孩子误杀了另一个孩子,因此导致家庭破裂。男主发现父亲与女邻居交往甚密,心生妒恨,而了解了父亲与女邻居的过往后,渐渐理解了父
自以为是的学生作品。在文本上运用了大量模糊的指代,企图调动观众共情来蒙混过关。把男人们心照不宣的苦涩作为电影的纽带,却没有呈现出更复杂更高级的男性形象。很可惜,电影里这群矫情逼让我完全无法感同身受。主角似有百般愁绪:对父亲婚外恋对象的觊觎,前启后合的两次落马,在瑞典街头没能挥出的痛击,帕金森之故握不紧的刀叉,妻子的不幸离世,代代相传的不告而别……也许“不幸会让人发光发亮”,但痛与不痛并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如果浮生既往,无需介怀,又何必酗饮旧事,满灌愁肠?这个议题太过终极。导演显然也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两个小时里什么都没讨论清楚,却还在结尾轻率地解答,和整部片子的氛围更差之千里。在类似题材的文艺创作里,屠格涅夫的《初恋》才是标杆。
叛逆期和青春期的重叠不只是生理的唤醒,也是精神走出襁褓的肇始。“弑父杀母”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荆棘,否则会陷落到双亲回环的人生中去。不信?女生过了24,男生过了28你再看看,很多人会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模样……甚至是悲剧。
大概好久不看小说的缘故,我看的还挺困惑。
更喜欢童年部分。那个夏天结束后,他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