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剧情介绍
小伟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妈妈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儿子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父亲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七月之痒火星需要妈妈生命国界提姆·狄龙:这是你的国家智者无敌秘密之家最佳婚姻黑夏第二季纳粹猎人第一季狼少女与黑王子OAD致命主妇我的生命之光冤罪不速来客五月槐花香进出口仲夏夜之梦白鲸我知女人心我的爱我的新娘梦男—死亡交友阁楼上的女孩村官不难当黑色皮革手册SP~拐带行~金宵大厦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维京传奇第四季洪熙官之魔门妖女与女人们的对话前路漫漫
一家三口的生活因父亲伟明被查出末期肝癌而改变。表面上平静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妈妈慕伶扛起家,却得不到父子的体谅。儿子一鸣收到美国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不敢告诉爸妈。他知道母亲不易,却不愿表现过多关心。父亲伟明则在迷雾之中暗自做出一个改变家庭命运的选择。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七月之痒火星需要妈妈生命国界提姆·狄龙:这是你的国家智者无敌秘密之家最佳婚姻黑夏第二季纳粹猎人第一季狼少女与黑王子OAD致命主妇我的生命之光冤罪不速来客五月槐花香进出口仲夏夜之梦白鲸我知女人心我的爱我的新娘梦男—死亡交友阁楼上的女孩村官不难当黑色皮革手册SP~拐带行~金宵大厦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维京传奇第四季洪熙官之魔门妖女与女人们的对话前路漫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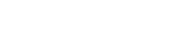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3+ 慕伶4、一鸣4+。伟明段非常减分,在试图通过影像宽慰人物、触碰情绪之前必须要明确苦痛是切实存在的。“幽冥”的本质应当是忠实纪录生命在特定境况下的颤音,而非把人物放置在设计意图明显到可以一眼望穿的虚境(对比《前进青春》的超现实段落)。
生活在广州的宁波人头一次在熟悉的粤语里听到乡音倍感亲切,导演对毕赣应该极为欣赏,所以寄托哀思介于写实与不断用媒介放飞自我暗示之间,导致后半段拖沓,也可能是删减的缘故。这个导演擅用媒介,可以说是我在广东见到唯一可以称是电影导演的人啦,可见我见了多少伪导演。可以期待他的技术,但或多或少我又感觉他的表达略简单,总有超脱不过港片的气韵,里面母亲面对两个垮掉的男人,真是伟大呀
210125 @芒果博纳乐和城.
家里也有同样配置,病人爸爸,我要出国读书,一切都特别熟悉,熟悉到看到那个杀甲鱼的妈妈甚至有点恍惚,好像就是我妈,只是我比导演幸运,后来一切都恢复了原样,但我好像一直无法摆脱这种状态,谢谢导演给了我一个出口,直到今天看完电影,我才懂一些事。
“那屋子里有个缝纫机,看上去还能用。”去年初也看了很好的处女作,所以这一点不算加分项。完成度不错的,意象编排我最喜欢小伟看到妈妈踩缝纫机那段,觉得戏剧技法很稳了。但是第二段兄弟情谊的落点好像消失了?
一鳴有中二病啊
不好意思,睡着了
Fake,从里到外的。
总感觉哪里不对,什么年代了还在瞒病情那套,自己住什么病房没点b数吗。然后亲友同事线没有,儿子学校线意义不明,绕回到遭遇变故的家庭关系的巡回、检视人生,重新发现,穿插点亦幻亦真的家国私货,以悦上意。ps:结尾的致敬是新人导演的流行的卖家人做法。(这么说似有不妥,但确实如此。)
观影前一度记不住的长片名 慕伶一鸣伟明 其实是一家三口的名字 故事三段式的讲述根据导演自己出国前考学 和归国后父亲生病 两段迷茫挣扎时间里的真实经历改编 家庭的相处 故乡的羁绊 像梦一样真实与虚幻交合 道出人生无奈无策的变数 手持摄影机的长镜和视角转换是亮点
本届FIRST影展剧情长片最佳。拍着胸脯说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华语处女作,时空性的完备程度秒杀所有阿彼察邦的拙劣效仿者。每场戏都有充足的信息量和解读空间,创作者有极其清晰的设计和考量,绝没有卖弄符号的心虚,剧作、表演和电影思维三者同时在场。一个在创作生态里越发“寻常”的家庭事件,用三人接力式的视角挖掘出每个成员的精神困境:死亡,青春,乡愁。联想和共情激起的思绪上下翻飞,无法止息。所有长镜头都没有露怯,有着丰富的细节和精准的调度。更不用说令人咋舌的景深镜头,对当下拍摄场景、人物内心乃至城市地貌都有深刻的认识。结尾与开头打通的幽灵视角直接把我看呆了,河濑直美《沙罗双树》的感动再次汹涌而来。自然、流动,让我耳目一新。
【林象·词语放映】很不错的处女作。三段式章节处理,分别从母亲、儿子、父亲三个视角记录了一段特殊的“别告诉他”亲人共处时光。虽然摄影比较粗糙,三人之外的配角线索交代不明。但导演的才华的确显露无疑。出片名的方式,在一个医院场景手持长镜头内完成探病/出院两个时间的叙事、儿子校园段落等都处理得清新脱俗,别具匠心。尤其第三幕探亲剧情的超现实部分,在破败的老房子里,父亲见到了故去的老母,在冥冥之中的指引下找到了坟地;儿子戴上父亲的画卷推开屋门便穿越时空与灵魂,化身为年轻时的父亲与中年时的奶奶交谈。可谓神来之笔。片尾电视的家庭录像既与片头的完成呼应,也是父亲灵魂视角的观察。很用心,值得鼓励
感觉回到了五年前在电影院看《路边野餐》时的感觉,三段式其实不是亮点,最重要的还是细节呈现,伴汤,一只鞋,倒影,烟盒…画面承接还算流畅,第三段现实与超现实的交替有点毕赣化,但确实挺有效的,指的是踏出影院时,还难以走出情境,特别是全粤台词与地区性之间的联系,走到大街上,看着三两行人时,后劲就来了。这种处女作粗糙感营造出的氛围,绝对比导演往后的作品灵气多了。
6/10。人物压抑的情感外化为狭窄的老城建筑、嘈杂的街道和天桥,多人关系的室内场景中许多突兀且不均匀的摇移、跟镜头来自重建回忆的在场的导演,或某种幽灵的视点,如画面紧随护士急促前往伟明对面的病房时剧烈抖动,一鸣和伟明谈论家里留学的经济条件时明灭闪烁的灯泡,都带有回忆的强烈情绪。小伟始终在逃离父亲濒死带来的痛苦:借厕所抽烟逃避广播体操,借神游在大片绿藤蔓吞没的白云山上逃离课堂;教师叫醒神游的小伟后继续讲阿基里斯追龟的寓言,永远领先的乌龟就像难以追及的记忆。为满足导演重建回忆和父亲心境的愿望,后半段海岛之旅变成了一个梦的迷宫:浓雾中堆积的废船,空旷无人的邮轮和岛上村落,老家里伟明与已逝的哥哥和母亲对话,一鸣看见缝纫机旁的母亲,都隐去死亡时刻和时空逻辑,当小伟与屋外的伟明隔着门窗对视,望穿了彼此心灵。
看前半段时觉得很有台湾故事片的味道,到了“伟明”那段就开始不知所云,导演以多个人物视角来构建故事,展现矛盾的多样性(这其实很像我写小说的方式,所以一开始观影时很兴奋),但后半段过于无力,流于空谈,原本扎实的叙事感质感倏然减弱。关于“超时空”“超现实”等问题,只能说有野心是好事,但不可否认稳扎稳打、细细密密地诚恳讲述本身就是值得推崇的可贵品质。2021.2.1,海口银龙。
主人公乘火車到浙江後,就不知道影片在拍什麼了。實際上堅持前兩節的實打實的風格,並不至於損傷影片的質感。2021年2月1日14:50於銀龍海秀VIP廳,廳中無他人。
不多见的墙内粤语电影,演员都挺棒。非常私人的家庭故事,也拍出了两代人的一些共通境遇,《一鸣》也贡献了最为自然舒适的校园青春戏。另外荒凉村落已然变成新导演超现实想象集中营,这部分如果延续原本的写实主义或许会更好。
不喜欢
青年导演的处女作,完成到这个水平,只能用惊艳来表述。2020北影节。
第一幕快速建立情感连接,第二幕生活流给足细节,第三幕超现实寄托情思,慕伶的忍气吞声,一鸣的少年幻想,伟明的落叶归根,在导演的时空变换和电影语言中呈现得克制而真诚,非常高级的动人,非常成熟的完成度。陈近南和一鸣之间莫名的cp感一定不是巧合,在厕所一起偷偷抽烟,在山顶互侃宏图美梦,那只遗失后又找回来挂在书包上的跑鞋,是彼此无需明言的青春期萌芽的佐证。只是像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一鸣也永远追不上病魔定下的时间,一支烟续下一腔苦,一幅画留下一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