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剧情介绍
站台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崔明亮(王宏伟)、尹瑞娟(赵涛)、张军(梁景东)、钟萍(杨天乙)是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改革开放初期,他们过的虽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却拥有相对丰盈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令他们见识到了各种新鲜事物,也使他们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认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当时间来到 1980年末时,他们发现虽然各自早已面目全非,却仍然一无所有。 相比如广州那样的沿海城市,如汾阳这样的中国内陆小县城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迟缓凝重的,可是崔明亮他们并没认识到这点。而他们为挣钱不断将自己的底线降低,则造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断层。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德里女孩第一季虚假的爱情有你才幸福纠正贵司的混乱!东北风云麻烦一家人第四季魔力之夜追爱自由行香格里拉下雪了吗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黑道家族第五季纯情房东俏房客春季特别篇痴鸡小队按响邮差的铃我们与天空的距离家怨致不灭的你第三季电影屁屁侦探再见亲爱的伙伴树下惊魂胖妞秘密商店诱拐法庭~七天~我的下位来宾鼎鼎大名第三季魔奇少年骨肉之躯阿加莎病房里的故事山田君与7个魔女月光光心慌慌8猩球崛起
崔明亮(王宏伟)、尹瑞娟(赵涛)、张军(梁景东)、钟萍(杨天乙)是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改革开放初期,他们过的虽是普普通通的日子,却拥有相对丰盈的精神世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令他们见识到了各种新鲜事物,也使他们对自身有了更多的认识,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然而当时间来到 1980年末时,他们发现虽然各自早已面目全非,却仍然一无所有。 相比如广州那样的沿海城市,如汾阳这样的中国内陆小县城改革开放的步伐总是迟缓凝重的,可是崔明亮他们并没认识到这点。而他们为挣钱不断将自己的底线降低,则造成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彻底断层。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德里女孩第一季虚假的爱情有你才幸福纠正贵司的混乱!东北风云麻烦一家人第四季魔力之夜追爱自由行香格里拉下雪了吗这个杀手不太冷静黑道家族第五季纯情房东俏房客春季特别篇痴鸡小队按响邮差的铃我们与天空的距离家怨致不灭的你第三季电影屁屁侦探再见亲爱的伙伴树下惊魂胖妞秘密商店诱拐法庭~七天~我的下位来宾鼎鼎大名第三季魔奇少年骨肉之躯阿加莎病房里的故事山田君与7个魔女月光光心慌慌8猩球崛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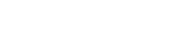
虽然出现了很多不符合时代的东西,但瑕不掩瑜,乡音、吵杂音、时代特征音,长镜头堆积,沉闷的基调,纪录片一样的时间线,缓慢的节奏,土的掉渣的群众演员,勾起了七零、八零后的那些记忆,构成了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这部没必要这么长
相比《小武》,它没有那么锋利却有这足够的暧昧,叙事上和情感上的暧昧模糊,充斥着不确定性,但大体的轨迹是可以预料的,那突然消失的人,忽然间就停下的梦,一切似乎像是闭合的,走了一圈终究是没走出去,成长的是心。最让我感动的是结尾,水壶里水开了发出的气鸣声与火车气笛声相似,与开头一群人在车里学火车叫相呼应,火车走了,载着的不是我们吧了。
太文艺了没法看下去。
看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是再也看不下去了……sigh
不装逼会死。
可能因为没有代入感,所以看完没什么感想,崔明亮那个总是赖唧唧的劲儿看着也让人喜欢不起来。
相比小武人物多跨度广,情节架构更加庞杂,几乎一场一镜,流行音乐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la vie n'est pas facile
最平淡的拍摄手法表现出了最为现实的残酷,迷惘的80年代,虽不及小武来的深刻,却已是身为导演最想表达的内心情绪。 干甚了这厮。。乃求了,麻求烦的不行,哇哇
封面很好,没看前就印象深刻。虽然贾樟柯为了营造自己要的效果故意用很多沉默或持续的镜头,感觉片子还是太冗长了。个人的感觉是较之《小武》要差不少。也可能是因为《小武》只需要从一个人的状态来反映那一类人,而《站台》则想反映那一代人。还是很有味道的一部片子。
用冷静的灰色调影像记录不一样的青春。县城文艺工作者面对生存困境,面对百无聊赖,最后还是朝着生活妥协,进入下一个无解的循环。这是用音乐照进现实的十年。
那代中国人所经历的人事物都有惊人的相似性,贾樟柯用了他几乎能想到的方法来插入他记忆中时代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的流行音乐和物件细节,越走越远的人总归还是回到了原点,本片不管是从技术还是创作主题上都算是导演最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了,期待《天注定》
贾樟柯应该是全世界第一个把海洋文化色彩极强的画面美学改造地极富有大陆底色的导演。本片是中国一个电影时代的巅峰。
水准超过《蓝风筝》,中国最出色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作者。每一个镜头都是一个故事,内容充实程度令人无法喘息。贾樟柯复原了风沙尘土笼罩下的80年代山西县城,让那一代人的青春梦想随时间漂泊于天边海角,也给了在2000年步入中年有了乡愁的他们一个半生归宿,让他们安歇半晌,然后继续上路。
含蓄、细腻以及黯然,在这部主题漫漶的电影中,贾樟柯用通篇的白描和旁观还原了一种隽永的乡愁,流浪的虚无、人际的脆弱、不由自主的命运,那些琐碎、断裂和看似随意攫取的场景,在时空的变迁中保持了温度。喜欢此片的镜头调度,人、物和空间有机的结合,推动叙事,又饱含深情。
贾导乐于陷在80年代土味乡村文学的泥沼里不能自拔。
贾樟柯电影里我最爱的一部。那种远远的旁观镜头,把人拉得远远的小小的,正符合我对画面的想象。觉得整部电影,每个画面都可单独独立成为震撼人心的照片。冷静的诗意,不可模仿的诗意,对这电影对我都正合适。
两个半小时的版本 还是老问题 情怀出来了 故事不够线性 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 你要表达的东西在如此平凡而共性的人物身上太难以被理解 可能我境界太低吧 我总感觉他是在用第六代的情怀拍第五代的题材 结果那个时间段是历史书上只留下寥寥几字 没有人愿意回忆 抹杀了某代人的黄金时代 他来书写/21.6 通过拍摄的素材看到了什么
在《小武》里就发现了,王宏伟长的真像我爸。他就跟电影里的崔明亮差不多,浑浑噩噩的过着没啥出息的小日子,几乎难以糊口。全靠我妈才勉强有个人样,真是个窝囊废啊。原以为我能好过他。现在坏了,我也光荣的成了窝囊废中的一员。
抱歉,贾樟柯的东西最多两分。